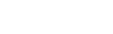贝多芬《第九交响曲》两百年
贝多芬《第九交响曲》问世前几天,遛着狗的维也纳市民意识到一切都会就此不同。在他们的狗儿闻着一块音乐会广告牌的时候,市民们看到的是一部“宏大”的新交响曲即将问世,“独唱和合唱将在终曲登场”,打破了交响曲只由管弦乐队演奏的传统。“路德维希·范·贝多芬先生将亲自指挥”的声明很难让人安心,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个聋子。在各个音乐社团的“好意协助”下,管弦乐团和合唱团的编制都被扩大。这部交响曲会很长,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交响曲。

贝多芬
但最令人震惊的细节是演出日期:1824年5月7日。
星期五?人们大呼小叫。没人会来的。统治阶级在周末都会去乡间别墅,而没有王公伯爵这些当时代表文化影响力的人出席,新作品的演出就没有意义了。贝多芬对此的解释颇为生硬,他只能订到剧院那天的档期,而且不管怎样,他希望这部交响乐不仅仅是为精英阶层而创作,而是要让真正的人民听到。他降低票价,取消着装规定,自己穿上了一件绿色夹克,因为他没有黑色正装大衣。此事件的方方面面都展示着贝多芬的意图:他想要颠覆既定秩序。
当晚的观众们都很兴奋,要求把第二乐章再演一遍。当天还是有一些艺术界人士留在城里;还有一位老伯爵从病榻上被人用担架抬过来。没有座位的学生们紧紧抓住墙边的扶手。紧张的气氛持续了五十多分钟。到终曲开始六分钟后,男低音歌唱家唱道:“啊!朋友,别再老调重弹——还是让我们的歌声,汇合成欢乐的合唱吧!”乐队给了他一小节时间深呼吸,然后男低音大声唱出“Freude!”,赞美欢乐。
合唱队起立,“alle Menschen werden Brüder”(四海之内皆兄弟)的歌词呼唤着革命——尽管这句口号因为否认君权神授,可能会使他们被捕。弗里德里希·席勒在1785年创作了这首满怀美好愿望的《欢乐颂》,而贝多芬为其赋予了群众的力量。从此时起它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势力,剑指所有国家的根基。席勒的诗篇是满怀美好愿望的乌托邦;贝多芬使其显得切实可行而且势在必行。观众们大声欢呼叫好。在音乐般的喧嚣声中还能听到有个警察在高喊秩序。一位独唱家拉拉贝多芬的衣袖,让作曲家转身看到欢呼跺脚的观众。贝多芬表示:“胜利在我手中,从此我可以直抒胸臆了。”
从那一刻起,接下来的两百年间,贝多芬的《第九交响曲》一直是打着各种红旗的社会改革者的集结号,从卡尔·马克思到凯尔·斯塔莫(Keir Starmer)。马克思将其描述为“世间欢乐的庄严弥撒”,而凯尔·斯塔莫最近对Classic FM表示,这部交响曲最能概括他领导下的英国工党:“它有一种使命感,而且又非常乐观。这是非常典型的工党气质。要让每个人,像贝多芬那样让每个人为了它而登上这个舞台……这是一种向更好的地方前进的感觉。”
这部交响曲曾为许多社会愿景服务。斯大林曾下令在苏联的每一个村庄演奏它。每年圣诞节前后,日本都会举办破纪录的“第九”音乐会,曾有多达一万名观众作为业余合唱共同唱响它。2005年,伊朗的阿亚图拉们以“不雅且西式”为由查禁了这首交响曲。
以伊恩·史密斯为首的罗德西亚白人统治政权将《欢乐颂》改编为国歌。欧盟在1985年也做了类似的事情,将席勒的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的博爱梦想解释为只适用于欧盟成员国及其公民,其余人类则只能被拘禁在铁丝网后等待遣返。当柏林墙倒塌时,伯恩斯坦在柏林指挥了一场凯旋音乐会,他用“Freiheit”(自由)取代了“Freude”(欢乐)。
小说家安东尼·伯吉斯(Anthony Burgess)在《发条橙》一书中将这部交响曲作为书中浪子的首选灵药,拉斐尔·库贝里克(Rafael Kubelik)为斯坦利·库布里克(Stanley Kubrick)在1971年的同名电影配乐时,进一步放大了这部交响曲的影响。女性主义音乐学家苏珊·麦克拉里(Susan McClary)在贝多芬这部高潮迭起的杰作中听到了“无法得到解脱的强奸犯爆发的令人窒息的狂怒”。她的论文促使诗人阿德里安娜·里奇(Adrienne Rich)写下了《终于被理解为一篇性文字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》,其中的一句富有弗洛伊德风格:“从自我的隧道中向欢乐高声呼喊”,暂且不论这意味着什么。作为最具普世意味的贝多芬作品,它对各种诠释都持开放态度。演绎这部交响曲时间最短的录音是39分钟,最长的是105分钟,这两者都不合理。中庸之道还差不多。

荷兰指挥家伯纳德·海汀克指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《第九交响曲》,2019年版
那么,我们对贝多芬当年的意图又有多少了解呢?他当时53岁,在奥地利人看来确实已经垂垂老矣,因为当时奥地利男性的平均寿命不到35岁。由于债台高筑,他接受了伦敦爱乐乐团低于市价的委约,并将1823年一整年都用来创作这部交响曲。但是到8月底时,他只写下了15分钟的音乐。慢板乐章又花了他两个月的时间。他去了一次巴登,以温泉疗养来安抚身体的疼痛,当他回到维也纳时,他拿着笔记本大喊:“我搞定它了!”
乐谱最后于1824年2月完稿,但贝多芬心存疑虑,提到过要写一个新的不带合唱的终乐章。“我犯了一个错误”,他曾经这么说。他曾经向柏林提出在那里首演这部交响曲,并且试图无视伦敦的合同,把这首交响曲题献给普鲁士皇帝。最终这部交响曲得以在维也纳首演,是由当地的一群有钱人赞助的,这表明贝多芬对平等主义的承诺并非处处平等。
贝多芬的犹豫不决丝毫没有削弱《欢乐颂》超凡脱俗的本质。伊戈尔·斯特拉文斯基可能曾经批评其旋律“平庸得无可救药”,伊恩·麦克尤恩可能曾蔑视它“像一首童谣”,但从《夏日将至》(Sumer is icumin in)到泰勒·斯威夫特的新歌,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别的音乐能像它这样,如此耐听又催人奋发。只要奏响两拍,全世界就能跟着唱起《欢乐颂》。
我想到有一件事可以证明《欢乐颂》持久不衰的意义。2020年3月,在新冠疫情造成广泛封城之后的最初几天,当时的人们不知道是否还能再见面,更不用说在一起演奏音乐了。鹿特丹爱乐乐团的成员在各自的卧室里通过Zoom来演奏贝多芬的《欢乐颂》,以维持自己的精神状态。这段视频被编辑后发布在YouTube上,短短几天内就突破了300万次播放,成为了互联网上有史以来播放速度最快的古典音乐。引用某个荷兰啤酒的一则老广告,贝多芬触及了其他作曲家无法触到的部位。
因此,如果凯尔·斯塔莫这位前市政厅音乐及戏剧学院的音乐学者在2024年能够让英国工党重新上台执政,他很可能会引用这部交响曲中对百万民众的呼吁,“这一吻献给全世界”。贝多芬希望凭借《第九交响曲》来消弭不平等。而随着这部交响曲迈入第三个世纪,它丝毫没有失去那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。